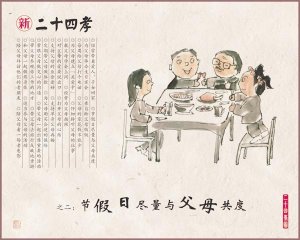admin
2019年03月14日
admin
2019年03月14日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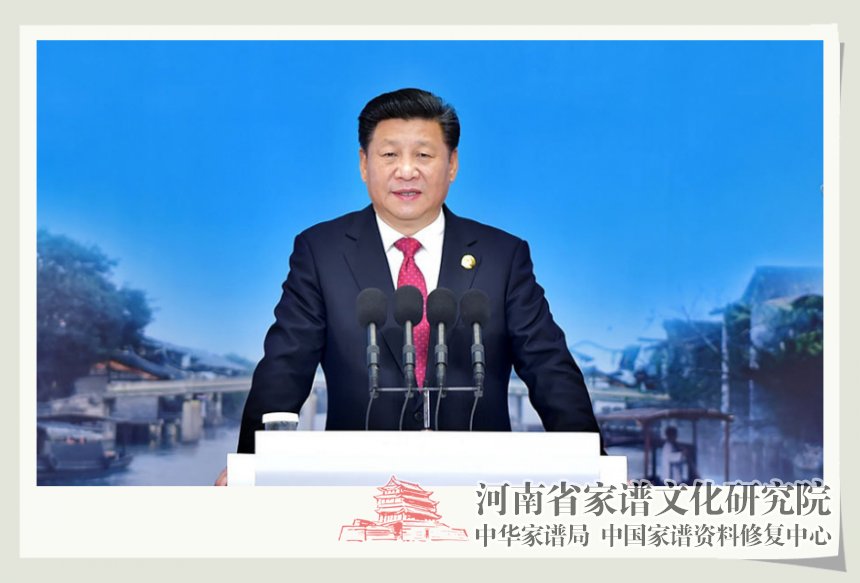
文化危機(jī)讓物質(zhì)財(cái)富猶如沙上之塔
習(xí)近平的儒生氣質(zhì),最直接的表現(xiàn)是善于立言:
為追思焦裕祿而填詞,為表達(dá)擁軍情義而作七律,勤奮地寫下大量反映個(gè)人思考的專欄著述,甚至還有“記得住鄉(xiāng)愁”這樣詩(shī)意的語(yǔ)言寫入中央城鎮(zhèn)化工作會(huì)議公報(bào)。
從他的個(gè)人經(jīng)歷、執(zhí)政風(fēng)格到文章思想,修齊治平、三不朽、“橫渠四句”等儒家經(jīng)典的使命追求,處處可見(jiàn)。
1949年以來(lái)的中國(guó)政治家,像習(xí)近平這樣將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置于人類共有精神財(cái)富的坐標(biāo)系中,指出其具有世界普遍文化意義,“智慧光芒穿透歷史,思想價(jià)值跨越時(shí)空,歷久彌新,成為人類共有的精神財(cái)富”,是不多見(jiàn)的。
更重要的是,他并未止步于文化態(tài)度上的致敬,在其執(zhí)政實(shí)踐中更是自覺(jué)地把中華歷史文化精華與中國(guó)特色社會(huì)主義緊密對(duì)接,在中國(guó)夢(mèng)以及內(nèi)政外交各個(gè)方面,都將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當(dāng)作“根”與“魂”。
習(xí)近平也講“揚(yáng)棄”,但不同之處在于,傳統(tǒng)文化更進(jìn)一步說(shuō)儒家文化,對(duì)于他而言并不是散發(fā)著陳腐氣息的沉重包袱,而是可以通過(guò)現(xiàn)代化創(chuàng)造,煥發(fā)強(qiáng)大能量、推動(dòng)民族復(fù)興的獨(dú)特“戰(zhàn)略資源”。
事實(shí)上,如果沒(méi)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和創(chuàng)新能力,選擇傳統(tǒng)文化作為戰(zhàn)略資源,風(fēng)險(xiǎn)并不小。
一個(gè)日益強(qiáng)烈的共識(shí)是,中國(guó)社會(huì)正面臨文化危機(jī),文化內(nèi)涵的空洞化,讓迅速積累的物質(zhì)財(cái)富猶如沙上之塔,越高越重,越容易崩塌。
中華民族正在不知不覺(jué)中喪失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。而這種危機(jī)的根由,遠(yuǎn)可溯及鴉片戰(zhàn)爭(zhēng)擊碎天朝的自洽幻景,近可論至改革開放后西方價(jià)值觀對(duì)人民信仰的沖擊。
一段時(shí)間以來(lái),電視劇熱播宮廷斗爭(zhēng)、爾虞我詐,官場(chǎng)、諜戰(zhàn)、職場(chǎng)、家斗也是常演不衰的題材,折射著犬儒主義盛行、人際關(guān)系惡化、社會(huì)誠(chéng)信缺失的現(xiàn)實(shí),顯規(guī)則被棄置一旁,“潛規(guī)則”卻大行其道;
圈子盛行,彼此謀利,參與其中的人都希求在制度之外找到獲取資源的渠道;
不勞而獲、一夜暴富被仰慕推崇,毒奶粉、毒大米、地溝油、瘦肉精頻頻出現(xiàn),更可怕的是不少人正逐漸對(duì)此見(jiàn)怪不怪、麻木不仁;
山寨文化幾乎成為“中國(guó)標(biāo)簽”,各個(gè)領(lǐng)域仿冒成風(fēng),這些人非但不以為恥,反而認(rèn)為能賺快錢就是英雄;
盲目從眾事件時(shí)有發(fā)生,理性的思考和表達(dá)卻少有人傾聽(tīng)。
20世紀(jì)90年代興起的“國(guó)學(xué)熱”,似乎讓人們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,各種“文化明星”名利雙收,漢服、唐裝招搖過(guò)市,大典、儀仗隆重登場(chǎng)。但很快就有人批評(píng)這種熱潮淺薄片面,只求功利實(shí)用。
當(dāng)代中國(guó)人對(duì)自己民族文化的理解,大多局限于“中國(guó)結(jié)”“功夫”“舌尖”等符號(hào)化的平面維度上,在信仰的高度上,在求善求美的高度上,卻少有耐得住寂寞的關(guān)注與追求。
政治學(xué)者鄭永年曾評(píng)論說(shuō),今天的中國(guó),很多人“既不了解西方,更不了解中國(guó),就是拿著一些工具性的東西在那叫嚷”。
還有學(xué)者舉出土耳其舍棄伊斯蘭文明卻又難以被西方文明認(rèn)可的文化困境,援引亨廷頓的觀點(diǎn)警示人們:這種不愿意認(rèn)同自己原有文明屬性,又無(wú)法被它想加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辱狀態(tài),必然會(huì)在全民族形成一種文明上、精神上無(wú)所歸宿的極端沮喪感。
這就是習(xí)近平這一代中國(guó)領(lǐng)導(dǎo)者面臨的嚴(yán)峻現(xiàn)實(shí)。特別是在新世紀(jì)之后,面向“民族復(fù)興”的目標(biāo),文化重建的呼聲更為強(qiáng)烈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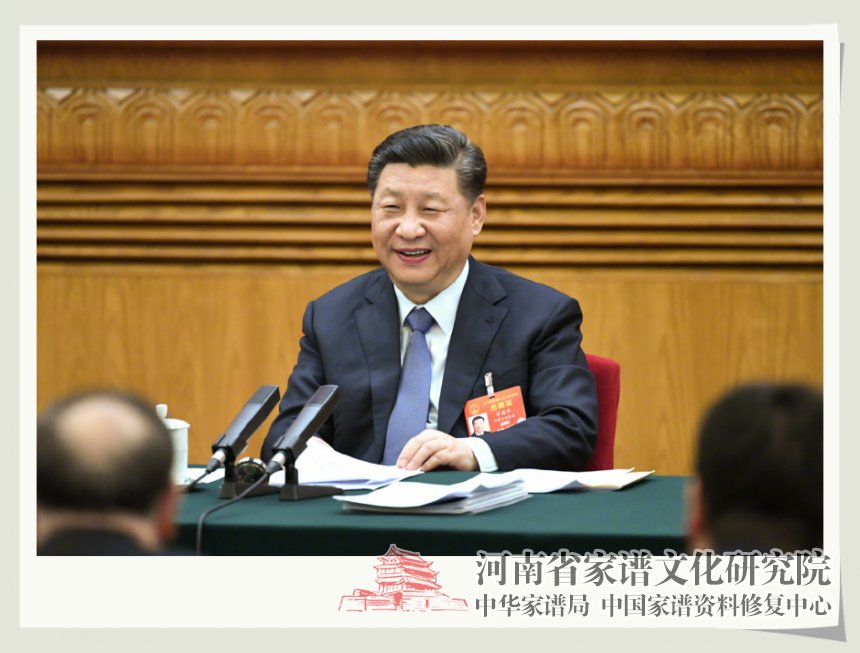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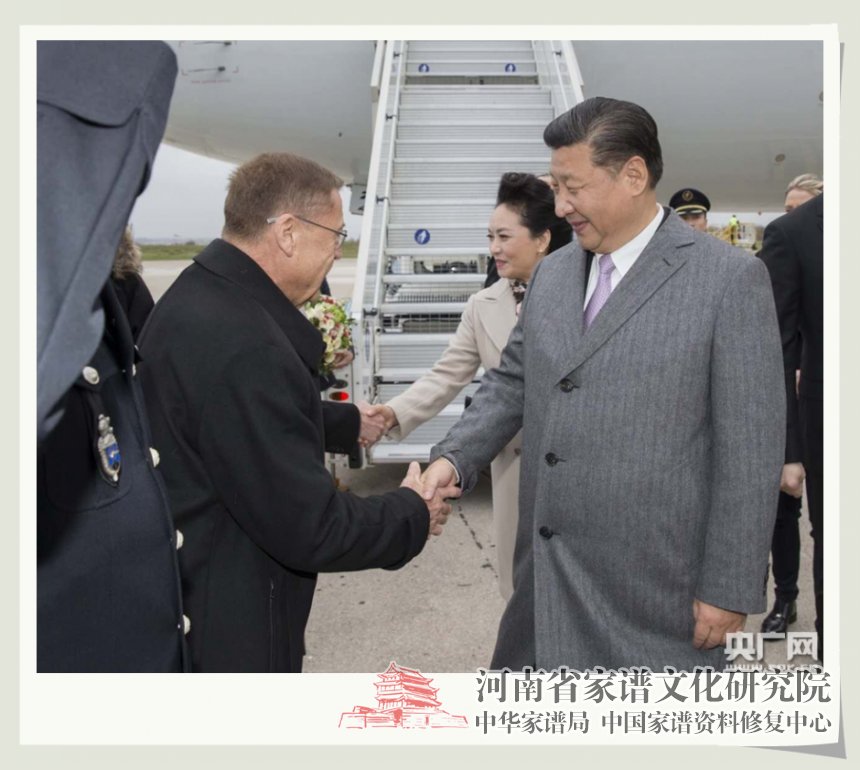
喚醒傳統(tǒng)文化之魅,又賦予其現(xiàn)代化之魂
傳統(tǒng)文化被視作救世良方,但從另一面看,有“國(guó)學(xué)熱”一地雞毛的前車之鑒,如何從儒家文化中汲取文化重建的正能量,亦是嚴(yán)峻挑戰(zhàn)。
有人說(shuō),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的圓融、自足,是一個(gè)“超循環(huán)”機(jī)制。
資本主義經(jīng)濟(jì)全球化的蔓延打破了這種“超循環(huán)”,進(jìn)而使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無(wú)法抵御帝國(guó)主義挾持著達(dá)爾文主義和叢林規(guī)則的侵略。
在這種境況下,傳統(tǒng)文化被救亡圖存時(shí)期的主流知識(shí)分子拋棄,而其后的文化封閉又讓斷裂的傳統(tǒng)文化缺乏更新的機(jī)會(huì)。
著名學(xué)者杜維明曾撰文說(shuō):“過(guò)去我們打倒孔家店、批判孔老二,人們把官員貪污腐敗、民眾貧窮愚鈍、新舊極權(quán)主義、錯(cuò)過(guò)了工業(yè)革命、沒(méi)能建立民主人權(quán)法治社會(huì)、不完善的市場(chǎng)經(jīng)濟(jì),等等,都?xì)w結(jié)于傳統(tǒng)之惡劣。
我們拿幾千年積累下的文化污垢同歐美文化中的優(yōu)質(zhì)部分作比較,把責(zé)任歸結(jié)到傳統(tǒng)文化,尤其是儒家思想與倫理身上,這顯然有失公允。”
孔子研究院院長(zhǎng)楊朝明也說(shuō),在對(duì)待孔子與傳統(tǒng)文化的問(wèn)題上,人們的態(tài)度形成明顯的兩極還是近代以來(lái)的事情。不少人將中國(guó)落后挨打的原因歸結(jié)為傳統(tǒng)文化的腐朽,強(qiáng)化和放大了人們對(duì)傳統(tǒng)文化負(fù)面影響的認(rèn)識(shí)。
于是在20世紀(jì)的一個(gè)時(shí)期內(nèi),中國(guó)形成了一個(gè)“反傳統(tǒng)的傳統(tǒng)”,似乎中華民族要擺脫苦難就必須摒棄傳統(tǒng)文化。
習(xí)近平面對(duì)的難題是,不能使中國(guó)成為文化的流浪兒、精神的乞食者,因此必須喚醒中國(guó)文化中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基因,同時(shí)又賦予其現(xiàn)代化的靈魂。
2014年9月24日,習(xí)近平在紀(jì)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(guó)際學(xué)術(shù)研討會(huì)上說(shuō),“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是一個(gè)國(guó)家、一個(gè)民族傳承和發(fā)展的根本,如果丟掉了,就割斷了精神命脈”。同時(shí)他也強(qiáng)調(diào),要努力實(shí)現(xiàn)傳統(tǒng)文化的創(chuàng)造性轉(zhuǎn)化、創(chuàng)新性發(fā)展,使之與現(xiàn)實(shí)文化相融相通。
他在全國(guó)宣傳思想工作會(huì)議上提出,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中包含著中華民族“最深沉的精神追求”“最深厚的文化軟實(shí)力”,可以凝聚和打造強(qiáng)大的中國(guó)精神和中國(guó)力量。
不僅如此,習(xí)近平還將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視作解決人類共同難題的思想庫(kù)。
他舉出了可以古為今用的15種優(yōu)秀古代思想:
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;
天下為公、大同世界;
自強(qiáng)不息、厚德載物;
以民為本、安民富民樂(lè)民;
為政以德、政者正也;
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、革故鼎新、與時(shí)俱進(jìn);
腳踏實(shí)地、實(shí)事求是;
經(jīng)世致用、知行合一、躬行實(shí)踐;
集思廣益、博施眾利、群策群力;
仁者愛(ài)人、以德立人;
以誠(chéng)待人、講信修睦;
清廉從政、勤勉奉公;
儉約自守、力戒奢華;
中和、泰和、求同存異、和而不同、和諧相處;
安不忘危、存不忘亡、治不忘亂、居安思危。
杜維明認(rèn)為,21世紀(jì)的中國(guó)更需要“自我更新的儒學(xué)”。
他的期待是,儒學(xué)要面向整個(gè)世界——
儒學(xué)第一期是從曲阜的地域文化、地方知識(shí)發(fā)端,經(jīng)歷數(shù)百年成為中原文明的核心、中國(guó)文化的主流;
第二期從中國(guó)文化發(fā)展到東亞文明;
未來(lái)儒學(xué)的第三期發(fā)展,要真正成長(zhǎng)為“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(shí)”。
“而這就要看儒學(xué)能否對(duì)整個(gè)西方文明、尤其是從啟蒙以來(lái)的‘啟蒙心態(tài)’作出回應(yīng),并進(jìn)而能否給人類社會(huì)提供有價(jià)值的東西”這恐怕不僅是一個(gè)學(xué)術(shù)研究者的期待,也是中國(guó)成為大國(guó)的文化使命與必然路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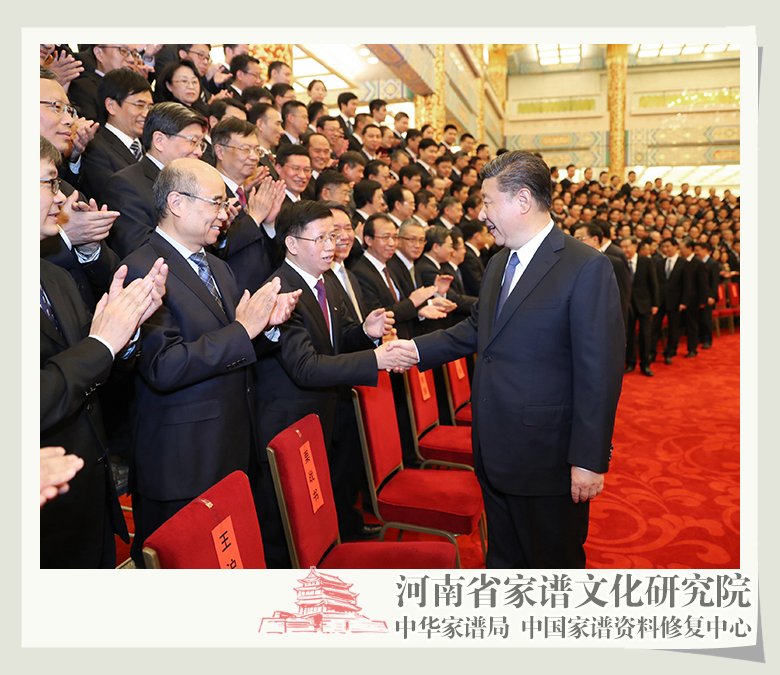

中國(guó)夢(mèng)不是空想,因?yàn)椤捌鋲?mèng)有根”
習(xí)近平善于援引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經(jīng)典的表達(dá)特點(diǎn)廣為人知,人民日?qǐng)?bào)社專門編寫了26萬(wàn)字的《習(xí)近平用典》一書,搜集了過(guò)去27年間習(xí)近平所有著述及重要講話中使用頻率高、能體現(xiàn)其治國(guó)理政理念的135則典故,每一則都以“三條微博”的文字量詳細(xì)解讀。
人民日?qǐng)?bào)社社長(zhǎng)楊振武談及編纂這本書的緣起時(shí)說(shuō),習(xí)近平用典,“常常古為今用、推陳出新,不斷激活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,賦予鮮活的當(dāng)代價(jià)值與意義”。
不僅是在表述中用典,習(xí)近平更是在治國(guó)理政的框架構(gòu)設(shè)中,將傳統(tǒng)文化精華作為重要思想源泉。“深入挖掘和闡發(fā)中華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講仁愛(ài)、重民